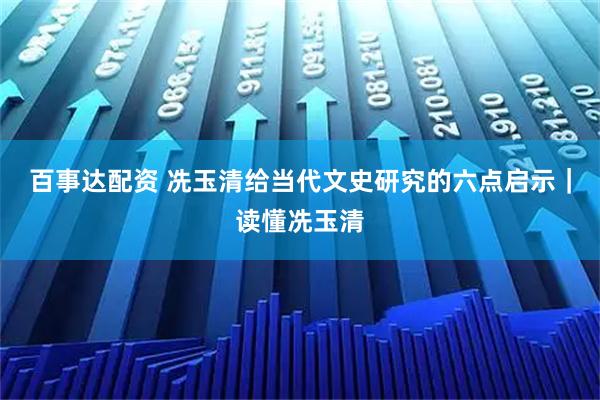
冼玉清毕生从事文献、文史研究,学术成果丰硕、学术精神丰满。其学术精神与研究实践,不仅成为我们在新时代开展文史研究的榜样百事达配资,也对当代文史研究工作应如何开展留下诸多启示:
一是要热爱乡土,饱含“乡邦情感”;
二是要躬亲勘探走访,身历亲闻;
三是要坚持文献收集与历史研究相结合,做到以文证史;
四是要抱“殉学” 精神,全身心投入;
五是要严谨慎重百事达配资,精细客观;
六是要扬己所长,特立独行。
全文如下↓
冼玉清学术实践对文史研究的启示
冼玉清毕生从事文献、文史研究,她的学术成果丰硕,令人钦佩;她的学术精神丰满,令人景仰;她的学术实践丰厚,为我们在新时代开展文史研究提供了诸多启示。
启示一,从事文史研究,要热爱乡土,饱含“乡邦情感”。冼玉清曾说:“欲人民之爱国,必须使其知本国历史地理之可爱,而对于本乡本土尤甚。所以文史学者,对于乡邦文献,特为重视也。”她是这样说的,更是这样做的。她是岭南文献的守望者,她的学术著作,大多与广东有关百事达配资,岭南文化占了很大的比重,已出版的著作有《广东文献丛谈》《广东鉴藏家考》《广东女子艺文考》《广东丛帖叙录》《广东释道著述考》《粤东印谱考》,已成稿的著作有《广东医学名人志》《近代广东文钞》《近代广东名人生卒大事表》《广东中医药书籍提要》《广东艺文志解题》等。通读这些著作,你会感到她心中饱含“乡邦情感”,一生钟情于乡邦文化,对乡邦是那么热爱,对乡贤是那么推崇,用自己的一片热心,将向来被视为蛮荒之地的广东历史文化推向学坛。对被誉为“百粤学者之宗”的东汉著名学者杨孚的推崇,她下了很大的功夫。在《杨孚与杨子宅》一文中,她不仅写了杨孚之政治思想、杨孚之文藻、《异物志》之著录、下渡村杨孚之遗迹、杨子宅之题咏、“松雪”二字对后代园林斋舍命名之影响;还作了“河南”以杨孚之得名、漱珠冈为杨宅故宅之订误的考证。她说:“杨孚为吾粤著书最早之人……名贤遗址,曰宅曰井者,皆与岭南大学相接,是则岭大之荣。保存光大,责在我辈,又岂止流连赏玩而已哉?”可见,她是把弘扬乡邦文化、彰显岭南先贤作为文史研究者之职责的。
启示二,从事文史研究,要躬亲勘探走访,身历亲闻。在治学上,冼玉清做到群书必亲检,史迹必亲睹,渊流必探索。她对研治的文化史迹,都争取做到身历、亲闻、过眼,无一语无来历。这一特点在她的学术著作《招子庸研究》《何维柏与天山草堂》《陈白沙碧玉考》《天文家李明彻与漱珠冈》《杨孚与杨之宅》中,都打上了深深的印记。如在游历过南海横沙乡后,她对向为学界认为不知身世的招子庸作了一个评语:“子庸生此半农半儒之家,可游可钓之乡,有能诗能文之父,故先天与环境,皆足以影响其一生。”她以自己的亲历之感,揭示了招子庸一生之真相。此后,她根据自己的身历、亲闻及研究,写出了《招子庸研究》一文,由引言、子庸传略、子庸之家、子庸之政绩、子庸在山东、四川之纪游诗、子庸之画、子庸之《粤讴》、《粤讴》之翻译、结论共九部分组成,对招子庸做了一番征文考献的工作。又如她在写《何维柏与天山草堂》时,与何维柏生平相关的云桂桥及天山草堂遗址就在岭南大学附近,而这也是她徜徉思考之处:“从岭南大学西行,经云桂桥,度蜿蜒数十丈之水松基,约五里抵小港乡,明直臣何维柏天山草堂遗址在焉”。“余主讲岭南大学,每与诸子诵维柏之为人,休沐之暇,辄相与信步小港,流连草堂。先哲遗风,仿佛尚在。”学者陆键东评价说,冼玉清以身历、亲闻、过眼为治学之重,可以说是为清代以后备受推崇的“考据之学”提供了鲜活的范例。
启示三,从事文史研究,要坚持文献收集与历史研究相结合,做到以文证史。这一点,以她对“粤讴”的研究最为典型。她既注重文献的收集分析,更注重联系文献产生的历史背景进行深入的研究。“粤讴是广东地区通俗说唱文学形式之一,它与南音、木鱼、龙舟,同属粤曲歌谣系统,而各有其特点,这一文学形式是19世纪中叶招子庸所创始。”为此,冼玉清对招子庸创作的粤讴进行了系统的收集、分析,做了专题研究。在《招子庸研究》一文中指出:招子庸作品的题材内容“多半诉说男女人爱情,以及一些沦落青楼被侮辱与被损害者的可怜身世。作者以委婉的笔调,写出被压迫者的凄楚心情,声调悠扬,语意悲婉,佐以琵琶伴奏的幽咽之音,珠江画舫,水上闻歌,怎不引起人们的激越之情?以故招子庸每创作一讴,马上不胫而走,成为雅俗共赏的粤曲形式之一”。但她又认为,粤讴这样活泼的一个文学形式,仅仅用来抒写男女之情,它的题材范围未免太狭隘了一些。由此,她广泛搜集文献,选辑了一册粤讴,写出了《粤讴与晚清政治》一文,其中有“反映广大人民群众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与迫害的粤讴”,有“反映广大人民群众反对封建统治者的残酷剥削与血腥镇压的粤讴”,有“反映资产阶级维新派改良主义的政治要求的粤讴”。她想借搜集这一类反映当时政治生活的作品,“作为研究中国近代革命史和文学发展的印证和补充”。她认为中国近代革命史的研究是多方面的,在文学上,特别在广东的通俗说唱文学这一方面,如何反映这一历史时期的伟大斗争,就是编者所欲研究的课题。她的这一研究,其实是做到了“以曲证史”或“曲史互证”。
启示四,从事文史研究,要抱“殉学”精神,全身心投入。“以学校为家庭,事业为丈夫,学生为子女”作为心志的冼玉清,将其毕生精力投入到文献、文史研究及国学教育之中,体现了伟大的“殉学”精神。在其最重要的著作《广东释道著述考》中,她花了十数年的苦功。该书起自唐,迄于现代,上下1300年,全面收集、评述广东僧人和学者关于佛教、道教的著述,仅仅是作为考订主体的佛道著述,就有500种之多。而为考订一书所阅读的著述,还要比原书多出几倍甚至十几倍。她以书(篇)系人,考释著者生平,著述主旨,适加案语,让岭南千年释道之迹,呈现于世人面前。该书博涉群籍,征引繁富,搜书之多,学养之深,令人钦佩。1953年暑假,冼玉清到北京游览,看过北京图书馆的藏书后,她竟从此日日到该馆抄书,早去晚归,达两月余之久。用她自己的话来说:“馆主任说什么僻书都让我看光了。”1957年,冼玉清随中山大学教师到华中旅行休养,经过杭州时参观浙江省立图书馆,她立即搬到图书馆旁的一间旅店住宿,日日到馆抄书,为“广东人的著作做提要,费时月余”。这是冼玉清为该书长年“手不停披于百家之编”的一个有力证明。
启示五,从事文史研究,要严谨慎重,精细客观。冼玉清在这方面为我们做出了榜样。她在治学严谨的基础上,能直指学人之误,成一家之言。如她在《六祖坛经》二卷中所作谨按云:“惟阮《通志》则著录《六祖坛经》三条:既作唐惠能撰,复作唐释惠昕及唐释法海撰。查《坛经》是惠能说,法海录,可谓为惠能撰,亦可谓为法海撰。惠昕则将不分门品亦不分卷之法海本分为二卷十一门,直是改编。阮《通志》谓为撰,误。宋《志》谓为注,亦误。惠昕宋人,阮《通志》谓为唐人,且列在法海之前,尤误。”又如她在《陈白沙碧玉考》一文中,以详确证据证明“白沙先生根本未尝被聘”。她写道:“按屈大均《广东新语》信为聘玉,盖未尝于本集核之。……宪宗未尝聘先生,下段有详确证据。”“袁枚以为宣德聘玉,尤为大谬。”“实则大均与枚皆才气横逸之文人,而非研精覃思之学者,文人好事,而束书不观,故有此误。”即使是对国学大家胡适的说法,她也敢于直言,提出不同意见。《菩提达摩南宗定是非论》是胡适根据巴黎国家图书馆所藏敦煌写本、编号伯希和(3047号)第二件的卷子,以及后来又在巴黎国家图书馆新发现的伯希和(2045号)第一件的卷子,校勘、汇辑而成。胡适对此项极有意义的成果甚为自得,据此进一步提出:神会是“南宗的急先锋,北宗的毁灭者,新禅学的建立者,《坛经》的作者”,并称此论“为发千载之蒙”。冼玉清经过详细考证,指出:“有关南宗七祖神会之阐扬,钱谦益在其《杜工部集》卷十五《秋日夔府咏怀奉寄郑监(审)李宾客(之芳)一百韵》注中,已详言之,沈曾植《海日楼札丛》卷五《禅门师资承袭图》更将此问题提出,而胡适自矜为发千载之蒙,可谓诬妄之尤也。”
启示六,从事文史研究,要扬己所长,特立独行。冼玉清不仅是著名文献学家,还是一位著名诗人。她在文献、文史研究中,充分发挥自己在诗作方面的特长,以诗纪史,每到一地,辄题一首。如1956年赴梅州、潮州考察时,所成之诗就有《出发潮梅》《增城途中》《车过西湖》《初抵汕头》《潮汕风味》《礐石中学》《初抵梅县》《过人境庐》《党群问题》《福利问题》《学习问题》《领导问题》等,既表达所见所闻,又传达感受感情,引起各方重视。又如在抗日战争期间,她写了100首七绝组诗,后编为《流离百咏》,分为8章:归国途中杂诗、曲江诗草、湘南诗草、坪石诗草、连州诗草、黄坑诗草、仁化诗草、归舟杂咏,平实地抒写了一位学者在抗战时期的流亡生活经历,展露了当时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虽然没有直接描写英勇杀敌的抗战场面,但不失为史诗式的抗战长卷。不少学者说,“冼子之学,为诗所掩”。粤中学者诗人罗球把《流离百咏》看成是可以“留与他年付史官”的历史文献。陈寅恪教授更认为这是“以诗证史”,不失为史学研究的好方法。在冼玉清送给他的《流离百咏》上,他写道:“大作不独文字优美,且为最佳之史料,他日有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者,必有所资。可无疑也。”由此可见,冼玉清的诗作,不仅具有文学价值,而且具有史学价值,她以自己擅作诗歌之长,巧妙用于文献、文史研究,令人深受启迪。
【作者】杨兴锋,系南方日报社原社长
【频道编辑】李晓霞 陈健鹏
【文字校对】华成民
【值班主编】叶石界 郭芳
【文章来源】《岭南文史》2025年增刊

翔云优配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