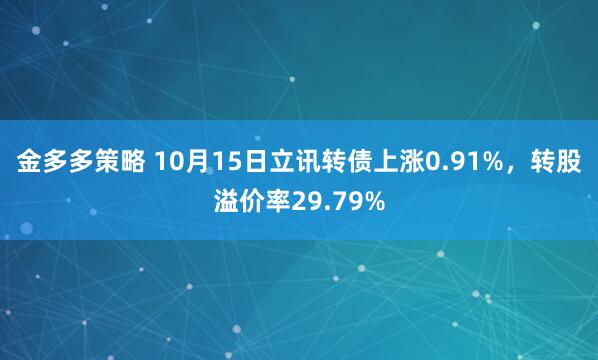✦景盛配资
图片
✦
✦
摘要
马克思的《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是一部内嵌着丰富方法论变革的哲学论著。在这里,马克思进入狭义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的历史现象学,他揭示出发生在经济的社会赋型中这种特殊的商品现象背后的价值关系异化为货币的本质。然而,更深的客观经济关系异化还表现为金钱异化为支配世界的权力。
作者:张一兵,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摘自:《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1期
本文载《社会科学文摘》
2023年第11期
马克思的《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以下简称《大纲》)是他实现第二个伟大理论发现——剩余价值理论——的重要经济学论著景盛配资,也是一部内嵌着丰富方法论变革的哲学论著。在全新的经济学思想实验中,爆燃起马克思认识中的多重革命火焰。在这里,马克思进入狭义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的历史现象学,他揭示出发生在经济的社会赋型中这种特殊的商品现象背后的价值关系异化为货币的本质。然而,这还只是走向资产阶级经济负熵构式中复杂经济物相化关系场境异化的开始。马克思突然发现,更深的客观经济关系异化还表现为金钱异化为支配世界的权力。
金钱异化为支配世界的权力
在《大纲》“货币章”中,马克思明确指出,人所创造的货币畸变为劳动交换关系异化的无形权力。也由于货币作为商品交换价值的象征,业已从劳动直接塑形和构序的商品使用价值的交换活动中,历史性地客观抽象为同质性的价值等价物,人与人的劳动交换关系也就在“此—彼”错位关系中事物化为可见的事物(金钱)与事物(商品)之间的关系。马克思深刻地指认,货币本身已经是价值关系异化。久而久之,不是它自身的货币的到场就开始变味了,因为,金钱从商品交换的镜像尺度、手段慢慢地变成了价值(财富)的一般代表。在这里,英磅还是英磅,美元还是美元,金钱本身没有任何改变,可它不再是自身,而畸变为所有财富的转换器。这是新的“此—彼”关系错位,也是一种新的不在场的伪在场性:金钱=所有不在场的财富。这是经济物相化关系场境存在论中发生的金钱篡位的重要事件和金钱世界确立的根本性构序支点。
在经济物相化的场境关系赋型和编码中,随处到场的金钱,现在不再仅仅表征没有在场的劳动交换价值,而就是财富的真实在场,人拥有多少金钱(“此”),就象征着拥有多少财富(“彼”)。在这个异己性的“此—彼”错位关系中的伪性编码意义上,金钱比直接的财富更具有在场性,因为,它可以换来一切可能到场的财富。马克思说,现在“货币是财富的一般物质代表”,这就在本质上出现了一个可怕的关系场境颠倒,即货币从中介性的手段(计算劳动量)变成人们疯狂追逐的目的(财富),这是人们过去面对全部生活直接需要的生存“爱多斯”的彻底脱型,现在一切人与物的存在,都只有一个“爱多斯”指向——发财致富。并且,货币从效用性的交换工具成为支配性的权力,在现实的经济生活中反过来畸变为统治人的外部力量。在经济物相化存在论的意义上,这将是历史现象学所面对的新一重“此—彼”错位关系,也是最难破解的关系场境转换。马克思说,恰恰是在这种颠倒的伪境之中,“货币从它表现为单纯流通手段这样一种奴仆场境,一跃而成为商品世界中的统治者和上帝”。原先人们创造出货币时,是将其置于可以随意驱使状态的商品交换工具,货币在商品交换中的初始到场是马克思所说的金钱服务于人的“奴仆场境”,可是现在,人所创造出来的“奴仆”却成了无所不能的金钱,金钱的到场业已畸变为一种不在场的支配性权力的无形在场。由此,金钱也成为经济王国中万物的唯一着色,现在,不是人驱使金钱,而是金钱驱使和支配我们,它现在就是私有制下世俗人间的统治者和上帝。
图片
在马克思这里,开始货币只是商品与商品交换的到场中介关系,可是后来它却变成了具有独立在场性的主体,畸变为支配一切的商品世界中的统治者和上帝,这个“我—它”自反性关系中的异化伪境也并不仅仅是一种经济拜物教的主观构境,而就是现实生活本身中发生的经济物相化编码和构序的客观存在论伪境。这也意指金钱拜物教的主观构境,其根据是现实经济关系本质的客观反转和异化。这里出现的辩证法,正是经济事物的消极辩证法,或者是“第二自然辩证法”,因为在这里,作为社会生活起初基础的物质生产中主体性的劳动辩证法,现在颠倒地呈现为商品、货币一类经济事物在流通和生产领域中自我运动的客体辩证法,它的规律是从无序返熵的自发构序中生成经济必然性的。依我的看法,这种人之外自在运动的“第二自然辩证法”,恰是资产阶级那个“自然法”的本质,由此才会出现将资产阶级生产关系视作符合人的天然本性,永恒存在的意识形态幻象。人与人的劳动交换关系场境现在客观地颠倒为事物(商品)与事物(货币)之间的关系存在论编码伪境,人的能力假性式地转化为金钱的事物性的万能,这就是资产阶级社会经济关系表现形式上特有的事物化。这种人与人的关系事物化为事物与事物之间关系异化的本质,恰恰是资产阶级社会中历史性发生的商品交换关系、货币关系和之后的资本关系,隐匿到经济物相化关系场境存在论中伪在场的事物性关系编码的背后,充当起不可见的无脸统治者。这也就是说,现在真正统治人们的力量是客观抽象出来并且异化和事物化的交换关系(价值—货币—资本)。统治现实资产阶级社会生活的“抽象(本质)”,恰恰是抽象劳动的等价关系—价值关系—事物的篡位(货币与资本物)—观念性—事物的象征—符号(信用)。
这样,货币作为人创造的工具成了人的主人。在这里,我们还可以进行一个比较分析,即同样是作为劳动技能和工序的客观抽象并反向对象化为外部物性持存的工具模板(编码),锤子和镰刀作为人创造的工具,它们就是它自身,它们的用在性效用会直接实现于劳动活动的重构之中,只是当工具发展到资产阶级生产关系支配的机器系统的时候,才会出现与劳动主体的异化关系问题。而作为劳动交换关系的客观抽象且反向物相化的货币,从一开始,它的物性实在就不是它自身,而只是在他性存在的正在消逝的东西上象征无法直接在场的劳动交换关系场境,所以货币从一开始就是劳动关系的异化(价值),后来会进一步发展为金钱权力异化和资本关系异化。在广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客观尺度中,这是很难描述的奇怪的关系颠倒,马克思想到,这当然是历史现实中发生的客观关系异化。这里,并不存在任何人本主义的本真性的价值悬设,货币最先作为商品交换的尺度和工具不是凝固化的理想化的“应该”,它作为一般价值等价物出现在商品交换活动中,是客观现实中真实发生的经济关系赋型;而现在,随着生产的社会化的发展,它慢慢地在资产阶级社会中从为人服务的手段变成了目的,从人自身的商品交换关系变成了支配人的权力,人通过劳动物相化创制世界的实践辩证法颠倒为“第二自然”中经济事物自发运动的消极客体辩证法。马克思直接指认,这是客观发生在现实社会经济关系中的颠倒与异化!必须指认,马克思这里出现在流通领域中的价值关系异化和货币权力异化,还没有深入到生产过程中的劳动异化的本质层面,或者说,这只是劳动异化“自乘”后在流通领域中的表现,这将是马克思进入“资本章”后逐步发现的历史现象学中更深层次的异化现象,以及之后《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劳动异化构式中的表象层面。固然,这种关系颠倒最初并不一定是发生在资产阶级社会之中,但它是后来资产阶级商品市场经济构式中异化的资本关系的前因,然而马克思发现,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却企图“把异化抽掉”,将这种社会本质的根本矛盾和经济关系事物化颠倒的在场性伪境说成是正常的和天然的,这不能不让我们警醒和反思。
从人的依赖关系到
事物化的物的依赖关系
相对于过去那种还没有被事物化的人与人的直接交往关系,当下资产阶级社会中人与人的关系的在场需要经过交换中介的事物化(颠倒),已经成为不可避免的现象。在这里,我们可以注意到,原先马克思在商品交换过程中指认的劳动交换关系颠倒为货币的事物化(I)颠倒,突然又被赋予了一种跳出具体流通领域更大的新的历史参照性,即第一大社会形式中人对人的直接依赖关系,整个资产阶级经济物相化空间编码和构序的经济关系场境,都是先前人的直接存在论关系场境解体和脱型后的事物化颠倒,这倒使马克思此处关于事物化的说明,成了全部资产阶级经济物相化中一切事物化现象的总体性确认。
商品、货币一类经济Sache不是简单的到场之Ding(物),也不是广义历史唯物主义非物像透视中人通过劳动塑形和构序出来的关系场境赋型的用在性,而是特指在经济的社会形式中经济关系颠倒为“对他们本身来说是异己的、无关的东西”,即经济关系场境物相化中作为“第二自然”本质的经济事物。在这个意义上,这个Sache就是经济物相化编码生成的特定经济事物。经济事物不同于一般劳动物相化塑形和构序起来的产品和工具一类普通事物,它已经是特定经济构式负熵进程中的关系场境赋型物。在这个意义上,事物化(I)是特指流通领域中经济事物化中的“此—彼”错位关系颠倒。这是马克思在《大纲》中,对资产阶级社会中特有的事物化颠倒现象的具体阐释。从这一详细话语分析看,在中文中将Sache译作“物”,显然是不准确的;而日本学界将Sache意译成带有主观显象意味的“物象”,将马克思区别于Verdinglichung(物化)所刻意使用的Versachlichung(事物化)译作“物象化”,也是不成立的。这当然也是我们前面已经讨论过的问题,通过劳动塑形和构序对象化在产品中的人与人之间的劳动交换关系,现在在反复发生的交换过程中被客观地抽象为交换价值关系,这种交换价值(价值)关系在充当价值尺度和工具中,慢慢地从等价物变成一般等价物,再从象征符码结晶为一个特殊的万能商品——货币。货币的本质,明明是人与人之间交换劳动(经济构式负熵质)的客观关系,但却成了追逐私欲的个人相互冲突的盲目返熵现象的自发整合结果,反向对象化为一个“异己的、无关的”先验于个人的经济事物。由此,再在经济物相化的特有交换空间中生成事物(金钱)与事物(商品)的伪存在论场境关系赋型和编码,当这种事物与事物之间的依赖关系成为统治人的外部力量时,也就会生成经济物役性的表象。这是马克思此处事物的依赖性关系的基础。在这一点上,劳动交换关系事物化(I)本身并非人的自觉活动的结果,而是一个与他们“毫不相干”的自发生成的经济事物辩证法(“第二自然辩证法”)的客观编码过程。实际上,对于资产阶级来说,这种推崇在人的主体意志之外自发整合运动的自然法则,也是他们所谓作为社会生活天然本性的“自然法”的意识形态基础,从重农主义生产的“自然性”开始,一直到斯密的市场波动中自发生成的“看不见的手”,经济物相化中出现的似自然性的“第二自然辩证法”就是资产阶级安身立命的法宝。
由此,才出现了马克思这里所指认的事物化颠倒中的双重转化:人的社会联系直接转化为货币—— “事物性的社会状态”,人塑形和构序外部世界的能力转化为“有钱能使鬼推磨”的“事物性的能力”。依我的判断,这个特定的经济Sache(事物),也正是狭义历史唯物主义中“物”的核心范畴。因为,这个事物是商品、货币和资本一类经济事物,它既不是自然对象物,也不同于广义历史唯物主义在一般物相化透视中将直观对象物归基于能动活动的塑形与构序关系场境存在,狭义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现象学所面对的经济物相化迷雾,是将关系场境重新遮蔽起来的经济关系颠倒后生成的经济事物及其伪在场性。科学地划分一般自然物、作为劳动塑形和构序结果的用在性事物与此处马克思指认的经济事物,是科学的批判认识论的重要任务。
图片
在这个经济的社会赋型中起决定作用的经济事物中,可见的商品、金钱物像制造出来的经济物相化伪境背后遮蔽着劳动交换关系,之后,它将魔化为“普照的光”的资本关系,成为整个资产阶级世界中真正的统治者。这说明,马克思在经济学语境中指认的狭义历史唯物主义构境里的经济关系和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异己经济力量决定社会生活和观念,并非指认一种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而仅仅是在经济构式负熵进程中的社会赋型,特别是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本质和特定社会中“第二自然辩证法”的运动法则(“自然法”)。狭义历史唯物主义的本质是一种科学的历史现象学批判话语,它在工业生产和科技革命的全新物质实践基础上,以资产阶级商品—市场经济物相化关系场境存在论世界为特定对象,深刻地透视了人与人的关系场境事物化为事物与事物的关系为基础的经济物相化,同时,历史现象学也以科学的批判认识论,透视经济物相化编码背后的客观异化逻辑和物化误认之上的经济拜物教。如果说,历史现象学中的异化概念,在此是从主体向度观察第二大社会赋型特别是资产阶级社会经济关系中,第一大社会赋型中在场的人与人的直接依赖关系和主体性劳动在商品交换活动中发生的“我—它”自反性悖结,而事物化理论则是从客体向度观察人与人的关系在同一个商品交换过程中颠倒为事物与事物的关系直接经济物相化现象。不同于不可见的异化关系,“此—彼”错位关系中事物化现象是直观可见的,或者说,相对于隐性存在的异化关系,事物化颠倒是更接近社会生活的物役性表象的,以经济事物的无序自我运动为本质的“第二自然辩证法”也是直观可见的。在一定的意义上,历史现象学中的异化构式是经济关系事物化现象的内在本质,而当人们在经济物相化迷雾中将“异化—事物化”中经济事物所具有的特定经济定在误认为物本身的自然属性时,这就产生了经济物相化中的物化幻象,它在日常经验层面所塑形的意识形态话语就是经济事物拜物教。
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对第二大社会形式的“事物的依赖性”的表征恰恰是外部的经济物相化编码假象。揭露这一“此—彼”错位假象,进而透视将事物化颠倒的结果视作自然性的物化误认(经济拜物教),正是狭义历史唯物主义构境中科学的批判认识论的主要解码任务。
当前内容可能存在未经审核的第三方商业营销信息,请确认是否继续访问。
继续访问取消微信公众平台广告规范指引 本站仅提供存储服务,所有内容均由用户发布,如发现有害或侵权内容,请点击举报。翔云优配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